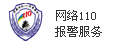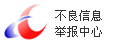近日,高淳区人民法院发布该院个人债务清理案件办理情况,以高淳法院的试点为标志,南京“个人破产”制度化探索正在起步。

在全国,《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》将于2021年3月1日起施行,《浙江法院个人债务集中清理(类个人破产)工作指引(试行)》也已发布。
“个人破产”走进我们的生活还有多远?
案例:给“诚实却不幸”的债务人新生
2020年6月,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发文,确定高淳为南京唯一一家“与个人破产制度功能相当的试点工作”法院,自此拉开南京针对“个人破产”试点序幕。截至今年1月初,该院审结个人债务清理案3件,涉及债务总金额近600万元,另有5件在审理中。
2020年12月30日,该院裁定批准,债务人谷某全力偿还73.2万元后,尚欠54.6万元债务予以免除。
卸下债务当晚,十几年不敢回家的谷某走进家门,抱着卧病在床的86岁老父亲号啕大哭。2003年受“非典”影响,谷某承揽的工程严重亏损。17年来,谷某除了弟弟去世当晚回家看过一眼,始终在外打工不敢回家。他的所有收入除看病、生活和子女学费外全用来还债,依然杯水车薪。
法院立案后,指定管理人对谷某所有财产、近3年财产变动进行调查,并核查债权人提供的所有财产线索。2020年12月,21名债权人表决通过债务清偿计划:谷某在清偿债务总额127.8万元的57.28%后,未予偿还的债务全部予以免除,并经一年信用考验期,恢复其信用。至此,南京首例个人债务清理案办结。
另一案件中,两名债务人均65岁,因经营亏损欠下50多位债权人400多万元。债务清偿计划明确,除预留两人医疗费用、基本生活费用每月共计3000元后,所有收入用于还债,如能8年归还本金的80%,未偿还债务将全部予以免除。
疑惑:如何避免成为“老赖”的狂欢?
“个人破产”与我国传统理念有出入,为什么要探索“个人破产”,这一制度会不会成为“老赖”的狂欢?
南京大学法学院特任副研究员张力毅认为,在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环境下,个人为企业债务提供担保情况较为普遍,由于个人破产制度缺失,一旦创业失败,企业虽然通过适用《企业破产法》得以免责,但企业家往往要以个人名义对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,经营风险由此可能转移到个人和家庭。
高淳法院党组副书记、副院长傅立新告诉记者,司法实践中,个人严重资不抵债的事实大量存在,个人破产制度的缺位,扼制了这部分人的创业创新动力。
“探索建立个人债务清理机制,可以在对债务人‘穷追不舍’的执行模式之外,提供一个债务人与债权人和社会多方共赢的债务清算模式。”傅立新说。
张力毅指出,从国外的“个人破产”实践来看,个人破产常常意味着一定时间和一定范围的个人失权,债务人的消费水平、职业资格、收入分配等都将受到严格限制。《深圳特区个人破产条例》也规定,个人破产后不得乘坐飞机头等舱、高铁一等以上座位;不得购买不动产、机动车辆;不得供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。
“另外,个人破产并非‘一破了之’,破产主要分为清算和重整两种程序,未来的个人破产,将主要是通过重整程序,为债务人设定较长时间的债务清偿期,从而最大程度地满足债权人的利益,并不会造成大规模的逃废债。”张力毅告诉记者。
作为南京唯一的一家试点法院,高淳法院在办理个人债务清理案件时,秉持“宽容失败、严防逃债”精神,要求债务人进行全面如实的财产申报;也对债务人三年内重大财产变动100%核查到位,债权人提供的财产线索100%核查到位,避免债务人利用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进行逃废债。
趋势:完善“半部破产法”,“类个人破产”试点正铺开
张力毅介绍,现行的《企业破产法》于2007年施行,早在立法之初,关于是否将个人破产纳入的争议就没断过,受当时社会发展状况所限,最终只施行了企业破产制度,该法也因此被称为“半部破产法”。近年来,学界对“个人破产”制度化的讨论从未停止。
2019年7月,国家发改委、最高院等多部门联合印发的《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》,研究建立个人破产制度,重点解决企业破产产生的自然人连带责任担保债务问题。这意味着停滞多年的个人破产制度建设开始提速。
除了南京,江苏的苏州,浙江、广东等地“类个人破产”工作试点也已铺开。事实上,国家层面对“个人破产”制度化的探索正在不断推进,“个人破产”立法呼之欲出。2020年5月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在《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》中明确,要“健全破产制度,改革完善企业破产法律制度,推动个人破产立法,实现市场主体有序退出”。